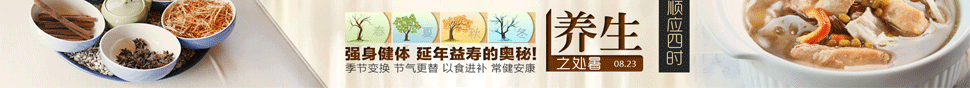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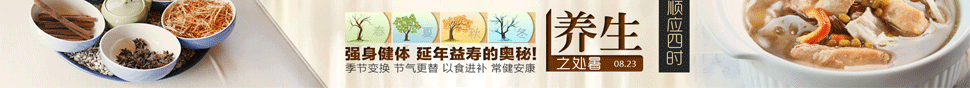
·论 坛·
我国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及其启示(四)
——沈自尹院士与中医“肾”本质的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研究
陈士奎
沈自尹教授(— ,浙江省镇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医院终身教授,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和著名中西医结合理论家。他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是开创中西医结合科研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医“肾”本质中西医结合研究泰斗。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年拜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年)为师学习中医,并共同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医藏象学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同年主持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国内首创的“脏象专题研究组”工作,后来,任脏象研究室主任。年经卫生部批准创办上海第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为首任所长;之后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等。年,成立了上海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沈自尹院士众望所归又担任名誉院长。
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沈自尹院士率领其团队一开始选择的研究方向便是中医药学重要理论之一“藏象学说”中西医结合;经过深入学习和研究,认识到藏象学说中“肾”为最重要之“脏”,如“肾”为先天之本,主生长、发育、衰老过程;肾为“命门”,肾阳温煦周身之阳,肾阴滋养周身之阴,为人体阴阳调节之中心;肾藏精,主生殖;主骨生髓;主水等。则“博观而约取”瞄准“肾”本质研究方向,始终坚持“博采众方”古训,与时俱进地及时引进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持之以恒地专一开展“肾”和“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研究已5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如“肾阳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应用”荣获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成为我国对中医学理论进行中西医结合科研典范。他领衔的“肾的研究”在我国科研史上高矗起一座中西医结合丰碑;他的举世闻名就是建筑在饱含他中西医结合智慧的扎实开展中医学“肾”和“证”本质等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科学研究上。
沈自尹院士率其团队50多年的科研历程、思路、方法、成果等研究,已有许多翔实专著,近年沈院士又发表文章[1],从肾阳虚(证)的研究、肾虚与衰老的研究、肾藏精与干细胞研究3个方面,阐述了“肾”本质研究的进展和成就,篇幅所限不再赘述。现仅就其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之意义和启示探讨如下。
1重视中医、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 沈自尹院士在中医“肾”和“证”本质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中、西医学理论为指导,以中西医结合思维为主线,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认为“中西医结合光靠临床实践、病例分析,而无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就深入不下去,只有下苦功夫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反转来指导临床,才会更好地带动治法、方、药的研究。”[2]他讲道:“一方面理论研究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产生,临床实践有待上升到理论;另一方面就是直接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把它反映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并可尝试把中西医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创立新的医学理论,形成新的理论学派”,“要有新的见解,新的论点”,“只有新的见解或新的理论才能把医学推向前进”[3]。强调“理论研究应以临床疗效为基础”,“要经受临床再实践”[3]。沈院士率其团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其研究的是中医基础理论,遵循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紧密结合,目的是发展中医学理论、促进中医学理论现代化,提高中医学理论指导现代临床实践防治疾病的能力;探索和构思的是创造中西医结合新理论。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首创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最需要理论培育。沈院士率其团队为培育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在中西医结合这片滋生新学科的沃土上,勤恳开拓,精心耕耘,播种育苗,硕果累累。
2善于理论思维,创造新理论概念 通过中医“肾”和“证”本质的系列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研究,发挥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沈院士以其勤于中西医结合思考的睿智,为构思中西医结合理论建设提出一些创新性理论概念[4],对于临床或基础理论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如何发挥理论(抽象)思维、创新思维、“构想”思维、创造或创新中西医结合理论等,具有示范和启发意义,在此根据其研究新进展再讨论如下。
2.1“生理性肾虚”年沈院士提出“衰老是生理性肾虚”[5],认为“仅以年龄制定衰老界限,或从外表来估计衰老程度,往往是不够全面,内在器官老化可以导致很多老年慢性疾病。关于衰老的原因和原理就有多种学说,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改变对于全身性衰老无疑占着十分重要地位。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生长、发育、衰老的过程,肾虚诊断标准如腰脊酸痛、腿软、双耳失聪、齿发脱落、性功能减退等,都是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的外象,可称为‘生理性肾虚’。其后又经“肾虚与衰老”系列深入研究,提出“如果将肾阳虚患者视作病理性肾虚的话,那么,正常衰老过程就可视作生理性肾虚。从两者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改变来看,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LRH)兴奋实验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为延迟反应,其反应曲线较为接近;两者血清促黄体激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LH-HCG)基值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老年组以血清睾酮(T)降低为主,肾阳虚组以血清雌二醇(E2)上升为特点,这两者变动的结果都是使E2/T值趋于上升。老年组和肾阳虚组的这些共同改变反映了生理性和病理性肾阳虚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建筑在肾阳虚衰这一统一的物质基础之上的。”[6]并通过肾阳虚证患者与老年人在甲状腺和性腺轴功能的比较研究,可见与老年人相差30~40岁的肾阳虚年轻患者,其甲状腺和性腺轴上的异常值与老年人相比较无明显差别,而且经温补肾阳药治疗后,异常值均有改善与恢复,进一步说明衰老是生理性肾虚。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7,8]:中药补肾益寿胶囊能使老年人和老年大白鼠的导致T细胞“自杀”的杀手基因FasL基因mRNA表达下调,可延缓老年T细胞凋亡,表明补肾法干预了衰老进程,并证明衰老是生理性肾虚[2]。中医、西医均“不见经传”的“生理性肾虚”和“病理性肾虚”新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医学关于“肾虚”的理论知识,而且丰富了老年医学理论。
2.2“隐潜证”由沈自尹院士首先提出。他概述“隐潜证”概念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对中医“肾”和“证”本质等进行系统的现代科学研究,首先发现“肾阳虚证”患者不仅存在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紊乱,而且具有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3条轴的不同水平、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而这3个内分泌轴上的功能紊乱,在内分泌领域里未能符合“病”的诊断标准,它属于一种隐潜性变化[2]。
通过10批哮喘患者的研究发现[2],采用温补肾阳法(“温阳片”含:熟地、生地、附子、肉桂、山萸肉、山药、巴戟天、仙灵脾、补骨脂)预防季节性发作的显效率,确实比对照组(包括空白片和小青龙治标药)为优,每批都能重复出这一结果。当对患者作内分泌研究时,发现哮喘即使无肾虚证候,其肾上腺皮质也有类似“肾阳虚”的隐潜性变化,即具有隐潜性肾阳虚证。进一步的免疫研究证明[2]温补肾阳药是通过提高抑制性T细胞(Ts)的功能,从而抑制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这是有效的免疫调控,从而使哮喘减少或预防发作。说明温阳片既可调解内分泌功能,也具有有效的免疫调控作用。因此,哮喘患者存在着轻微的或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以药测证”,用温补肾阳的“温阳片”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纠正其内分泌和免疫功能轻微或潜在的变化,可认为哮喘患者存在的轻微的或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是“隐性肾阳虚证”。另如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症,从微观辨病,有水液积聚、肾功能损害等,59%患者临床上出现阳虚之寒象,如怕冷、夜尿多、面目虚浮等,中医对水液之积聚形成一向有独到的认识,产生原因是由于阳气不足,不能温化水液之故。用“温阳利水”法可利水排石,治疗该症例,治愈率达71%。根据“以药测证”原理,也可认为该症属于“隐性肾阳虚证”。
于是便产生了“隐性肾阳虚证”这一微观辨证新概念。它指的是:根据“肾阳虚证”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相关变化特点,从实验室检测的微观指标运用中医理论思维进行辨证,并按“以药测证’法加以证实“隐性肾阳虚证”的客观存在。
“隐潜证”概念,是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理论思维相结合研究的知识产品;标志着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医传统“证”概念的科学认识,引起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如研究证实脾虚证、血瘀证等,都存在按中医传统宏观辨证方法“无证可辨”者,而根据已被学术界公认的各种“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特征,通过实验室微观检测却可表明存在着“隐性脾虚证”、“隐性血瘀证”等。概括之则统称“隐潜证”。推动了中医学“证”、“辨证方法”、“辨证诊断”及“辨证论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隐潜证”发明的科学意义和提示:“证”也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有助于早期辨证论治。表明在中医学“证”的研究中,实行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等现代科研的必要性。不通过现代科学实验(微观)研究则不会有“隐潜证”的发现。
2.3“微观辨证”微观辨证属于方法学范畴的新概念,也是中医辨证学及中西医结合诊断学新概念。沈自尹院士给其下的定义是:“微观辨证,就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技术检测的微观化的指标来认识与辨别证。”[2]
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在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技术、方法系统研究“肾”和“证”本质过程中,证明中医学的“证”及其变化是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并构思发明了“隐潜证”,在积累大量观测资料基础上有证据地提出的“辨证”方法新概念。他进一步解释: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他们的长处,在深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检测指标,并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从而弥补传统宏观辨证之不足,并实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提高辨证水平。[9]
“微观辨证”新概念提出的科学意义和提示:(1)是对中医辨证诊断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和发展。(2)“辨证”方法不要局限于传统的宏观辨证方法,仅靠传统的宏观辨证方法,难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隐潜证”;努力探索、研究如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隐潜证”的方法,对促进中医辨证学及“病证结合”诊断、辨证论治发展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3)为“隐潜证”、宏观辨证“无证可辨”(有病而无症状)、证候不明显(有症状但构成“证的诊断要素”不齐备或不甚齐备)、证候复杂以致辨证困难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微观变化尚未形之于外等情况提出了辨证方法,指出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4)推动了中医学“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及临床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研究,以及辨证诊断客观化(寻找实验室检测指标)、标准化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辨证诊断或病证结合诊断标准)等。50多年来,在沈院士首创的“隐潜证”、“微观辨证”新概念启发下,各中西医结合学科为揭示“证”的现代病理生理学基础、寻找“证”的实验室定性、定量检测指标及其检测方法等作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并发现了一些微观辨证规律和有价值的实验室客观检测指标等。展示了“证”本质的“探微索隐”中西医结合研究广阔前景。
“探微索隐”概念,首见于唐代中医学大家王冰(约公元~年,号启玄子)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该《序》讲道:“然刻意精研,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傑,时时间出焉。”[10]这一论述,强调了对《黄帝内经素问》“刻意研精,探微索隐”的重要意义:只有对中医学的经典专心致志的精心研究(“刻意研精”),并能努力探究其深奥、隐秘的道理(“探微索隐”),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其精髓和要领(“识契真要”);用其指导临床实践则可达到诊疗技术精进熟练(“目牛无全”);运用经典著作的理论精髓指导医学活动,常常可取得成功(“动则有成”)。如此一来,则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闻名于世的杰出人才就会不断出现(“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其中,“探微索隐”乃王冰精研《黄帝内经素问》,探骊得珠之真知灼见,代表了王冰对学习和研究中医经典著作的一种学术思想、观点和方法论。
对王冰所用“探微索隐”之内涵,中医传统上多按训诂学、考证学、注释学等加以解释,如《王冰医学全书》的释词是“互文句,即‘探索微隐’,探索精细、深奥(道理)。微,精细。隐,隐深,深奥。”[11]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微”也指“微观”“微观世界”;“隐”也指“潜伏的”“藏在深处的”。或许当年王冰已不满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宏观世界或宏观层次的研究,期望中医药学深入对“天人合一”的天、地、人的微观世界、微观层次,以及对阴阳、五行、脏腑、藏象、经络等中医学理论进行微观研究,从而提出了加强中医学“探微索隐”的微观研究发展方向。
联想沈自尹院士在探索“证”本质过程中,率先提出“隐潜证”、“微观辨证”等新概念,恰恰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探索“证”的微观病理生理变化和“证”在微观隐藏的或潜伏着的未知“奥秘”的结果。从唐代中医学大家王冰提出“探微索隐”研究思路与方法论,到当代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提出“隐潜证”、“微观辨证”新理论方法,既探微—探索微观辨证,又索隐—探索隐潜证,不仅是文字对应,两相契合,惊人的思路默契;王冰当年提出要“探微”,沈自尹院士提出了“微观辨证”;王冰当年提出要“索隐”,沈自尹院士探索出了“隐潜证”;“探微”与探测“微观辨证”;“索隐”与发现“隐潜证”,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真正体现了传承与创新发展了王冰“探微索隐”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也可以说沈自尹院士用“微观辨证”和“隐潜证”的研究,为“探微索隐”做出了现代科学的诠释,为注释或解读王冰提出的“探微索隐”开创了新纪元,使“探微索隐”方法论在现代科学层次上得到实践,真正实现了或实现着唐代伟大中医学家王冰所追求的“探微索隐”研究中医药学的梦想。[12]可见沈自尹院士乃真正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典范。
2.4“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即指传统中医辨证,主要是通过宏观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患者的信息,运用中医理论分析、判断、推理而做出“证”的诊断。沈自尹院士认为:中医“宏观辨证具有鲜明的整体观念,讲究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比之西医的局部观点是有明显的优势,其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甚为典型,有时部分表现而不易辨别,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2]因此难免有其局限性。微观辨证是对宏观辨证的补充;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被学术界认为是对中医传统“辨证”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飞跃,它使中医的“辨证”理论与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隐潜证”“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概念的发明,以及微观辨证方法的探索研究,是中西医结合创新性研究的凸出表现之一,是创新发展中医辨证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传承与创新发展古代著名中医学家学术思想、中医学方法论的典范。它对中西医结合或中医药科研均带来深刻启发,都应将原本为古代中医学家研究和发展中医药的思路方法“探微索隐”,运用到科研实践。
2.5“阴阳常阈调节论”《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沈自尹院士通过“肾阳虚”(证)的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有时表面看来阴阳是平衡的,其实是处于低水平的平衡,如肾上腺皮质分泌减少时,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则应增加,但肾阳虚患者以上两种激素的分泌都低,说明肾阳虚患者垂体与肾上腺皮质虽处于平衡态,但属于低阈水平的平衡,并非正常。所以,调节阴阳“以平为期”,不能只使阴阳达到低水平的平衡,而是要将低水平的平衡,提高到正常水平的平衡。正常水平的平衡是生理状态,称为“正常阈”。调节阴阳应以达到正常阈为目的。即“阴阳常阈调节论”[13]。这一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和实用价值,正如沈院士强调:治病不能以低水平的暂时平衡为满足,更不能以症状缓解(而内部仍处于不平衡,或失去了固有的调节能力)而被迷惑[13],含义深远。可见“阴阳常阈调节论”为“阴阳学说”的现代研究提出了重大命题。
综上所述,沈自尹院士率其团队是开创中医学基础理论及中西医结合理论现代科学研究的先锋,他开创的“肾”和“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引领了全国中医学理论与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向着微观层次不断深入发展,为揭示中医理论的现代科学认识和创建中西医结合理论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为开展中医学理论及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探索了思路与方法,其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和训练的是:他的科研活动总是从中医学理论出发,以中西医结合理论思维做桥梁,以构思中西医结合理论(概念)为落脚点。心里总是装着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他说:“中西医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形式,但必须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作有机的结合。”[2]
参考文献
[1]沈自尹.中西医结合肾本质研究回顾[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32(3):-.
[2]董竞成,蔡定芳主编.肾虚与科学———沈自尹院士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心路历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7-8,-,,.
[3]季钟朴,侯灿,陈维养主编.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5-37,.
[4]陈士奎.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概念的创造与评介(一)
[J].中西医结合杂志,,11(1):44-46.
[5]沈自尹.肾阳虚、老年人的内分泌研究[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4):35-37.
[6]王文健,沈自尹,张新民,等.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男性)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初步观察[J].中西医结合杂志,,2(3):-.
[7]沈自尹,陈剑秋,陈响中,等.老年人与“肾阳虚”患者的甲状腺轴功能对比研究[J].中西医结合杂志,,2(1):9-12.
[8]王文健,沈自尹,张新民,等.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J].中医杂志,,27(4):32-36.
[9]沈自尹.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J].中西医结合杂志,
,7(5):.
[10]王冰撰.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卫生出版社,
:5-7.
[11]张登本,孙理军主编.王冰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6:7.
[12]陈士奎.“探微索隐”今释〔N〕.中国中医药报,3-06-24(4).
[13]沈自尹.从垂体-肾上腺轴讨论阴阳常阈调节论[J].上海中医药杂志,,(5):3-7.
(收稿:-10-13)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700)
Tel:-,
E-mail:wawapapa9
.

